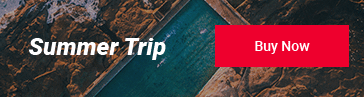快来看孕妇禁忌食物一览表(18种天然打胎药)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9-14
宫斗剧有三宝:中毒、流产、没安保。那么,中国历史上真有那些花样百出的“堕胎神器”?
.jpg)
按:宫斗剧有三宝:中毒、流产、没安保那么,中国历史上真有那些花样百出的“堕胎神器”?本期推送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教授的大作《堕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日常避孕抑或应急性措施?》,该文英文版发表于《明清中国》。
(Late Imperial China)2010年第31卷第2期,中文版载于《中国乡村研究》第9辑(2012年),译者为张宇为了阅读方便,本篇省略了注释,有需要的朋友请查找原文……长文预警……堕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
日常避孕抑或应急性措施?- 苏成捷 -
前言 两类不同学科的著名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堕胎这一行为是经常实践的,虽然他们依据的资料不同,且目标各异第一类主要是人口历史学家,如李中清(James Z. Lee)、李伯重以及王丰他们认为持续的系统性节育是中国人口制度的特色,而堕胎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既然中国几个世纪以来都在进行“理性”(rational)的计划生育,那么中国无需经历如西方的转折期,即从自然生育(natural fertility)向现代化生育控制(controlledfertility)的过渡。
根据李中清与王丰的论述,对中国人而言,从长期存在的传统节育实践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政府施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其间似乎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简单而顺利的转变第二类是包括白馥兰(Francesca Bray)、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在内的性别历史学家。
她们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一夫多妻制的精英阶层的家庭生育策略,但是她们的论述比起上述人口历史学家要更加精微细致,涉及范围比较小具体而言,白馥兰认为精英阶层的女性可以在妊娠早期使用堕胎药(委婉称为通经药)来中止怀孕(委婉称为月经不通),因为正常的月经来潮被认为是女性健康与生育的基础。
生育控制技术使得精英阶层的妻子免受怀孕之苦,从而将生育的任务转移到家中的妾或者婢女身上尽管存在诸多相异之处,但是这两类历史学家都认为,在明清中国,至少有一部分女性是可以依靠堕胎来进行节育的这一观点似乎是建立于传统的堕胎方式是安全、有效且易得之的前提之上。
这种看法,李伯重表示得特别明确如果事实如此,这些说法将对中国历史学科内部的一些子学科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如人口、社会性别、性行为、法律和医药研究等等而且,正如王丰与李中清所言,中国社会过去是否进行或者怎样进行生育控制,应该会影响我们对于中国今天人口政策的理解。
基于上述原因,明清时期的堕胎行为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两类历史学家的论述听起来颇有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进而增加了其说服力人口历史学家想象着明清时期的中国人拥有了充满现代标志的行为方式,并远远早于欧洲他们的观点无疑是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等学者关于中国与“近代早期”西方的对等(甚至是优于西方)关系这一主题的变体。
同时,性别历史学家论证了明清时期一些妇女在生育方面的相当大程度的能动作用甚至享有自主权,即便是以剥夺其他妇女为代价的(“并非所有女性都是自己子宫的牺牲品,女性可以也确实曾经行动起来控制自己的生育”) 高彦颐 (Dorothy Ko)、曼素贞 (Susan Mann) 等学者关于精英阶层女性在儒家父权制体制下追求自强与自我实现的主题,影响了白馥兰和费侠莉等学者,之后她们发展了这一主题,进一步包括了生育控制方面。
很多人都愿意相信上述的两种观点,但是我认为这两者都有谬误之处,至少在堕胎方面是如此为免于误会起见,首先我将明确在几个方面我是同意以前尚未研究的我同意某些传说中的堕胎方法是已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堕胎药例如,正如很多学者所知,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列出了许多据说可以用来堕胎的草药、动物和矿物成分。
我也同意人们有时试图打胎,至少其中的一些方法,至少在某些时候是会如愿起作用的但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是以前的研究中关于这些方法的安全、功效以及易得程度的论述——也就是妇女求诸于这些手段的实际情况我相信传统的堕胎药(主要的使用方法)危险且不可靠,通常都需要专门知识才能获得并使用,而且常常费用颇高。
在这种情况下,堕胎并不是一种计划生育的有效方式,也并非一种女性自强的途径相反而言,堕胎是一种处理危险情况的紧急干涉手段帝制晚期的文本资源大体上将堕胎置于病危或社会性的危机(例如因通奸而导致的家庭矛盾)的语境之中,前者所指涉的是怀孕危及妇女的生命,后者意味着怀孕暴露了一个女性的婚外性行为。
这两种危机情境中的堕胎现象,都可见于明代小说《金瓶梅》在第33回关于堕胎的第一个片段中,西门庆的妻子吴月娘怀有五个月身孕的时候,在楼梯上滑了脚扭了腰,开始腹中剧痛,生命危险她因此唤来一名女草药师,女草药师给了她没有说明具体成分的“两服大黑丸子药”,用酒吃下来打胎。
堕胎药起了作用,月娘打下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并且恢复了健康考虑到这部小说因果报应的逻辑,这个情节将西门庆屡教不改的滥交纵欲行为与他无法有男性继承人的事实联系在一起他的放荡造成了没有后代,因为他的健康受到损伤,这也是对他罪孽的报应。
在关于堕胎的第二段情节里(第85回),西门庆的妾潘金莲因与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通奸而怀孕(小说发展到此处,西门庆已经因服用过量的春药致死)潘金莲急于中止怀孕以此掩饰她乱伦的通奸行为,所以她的情人从妇科医生胡太医处设法得到了打胎药。
胡太医凭直觉感到陈敬济要找什么,但是他含糊地夸耀自己安胎的本事当陈敬济表明他的需求时,胡太医故作恐慌,“人家十个九个只要安胎的药,你如何倒要打胎?没有,没有!”只有当陈敬济表示要以重金贿赂酬谢时,胡太医才放下伪饰,给了他充足剂量的打胎药。
潘金莲服药后在尿桶中将胎儿打下这个堕胎情节包含着反讽的转折:潘金莲在整部小说中都渴望可以为西门庆传宗接代,但是当她终于怀上的却是陈敬济的骨血,且必须将它打掉吴月娘堕胎的情节是病危后果的一个例证,即一个孕妇的生命濒于垂危。
(另一个相似的情况就是当一名妇女因疲劳过度或者她的健康因多次怀孕受损以至于担心再次怀孕生育白馥兰和费侠莉所引用的医学材料记录了这种治疗性堕胎)对比而言,潘金莲的堕胎行为则是一个关于社会性危机的情况的例子,即一名妇女试图终止怀孕以防奸情的泄露。
这可以在清代法律文本中见到,也可见于关于不安全堕胎的中国现代医学报告中《金瓶梅》是小说,但是这两种关于疾病和通奸的情形解释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多数有文件记载的堕胎实例而另外突出的一点是,这两个情节都涉及一定要从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处获得打胎药。
换言之,小说将堕胎描述成一种专业知识,而非某种司空见惯的女性传统除此之外,人类学家还记录了第三类情况下的堕胎,他们通过与年老的农村妇女的交谈记录了在现代避孕技术到来前的生活:一些妇女因为过度贫穷和体力疲弱试图中止怀孕来避免生育更多的孩子(李中清和王丰可能会称为“早停”行为)。
但是因为惧怕丈夫与公婆的反对,她们秘密进行既然这些妇女担心过多的生育会带来健康方面的后果,她们的行为与文案记录中的疾病危机颇为类似我将在下文分三部分进行讨论首先,我将评价人口历史学家和性别历史学家的观点,尤其是他们的。
定性证据(qualitativeevidence),我认为他们自己的材料证据实际上推翻了他们的最终结论同时我也将阐释人类学家的相关发现然后,我将提供清代司法资料中的新证据,其中提供了很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堕胎的安全、可靠、易得程度,以及妇女在什么情况下会尝试堕胎。
清代案例显示了这样的事实——即使对那些急切需要堕胎的妇女来说,堕胎药也未必是可获得的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将综述现代医学报告中持续存在的中国妇女使用传统方式进行不安全堕胎的例子,这些例子一直持续至今这些医学报告补充了清代法律案例,这两方面的证据都有力地驳斥了对中国传统堕胎方式的乐观情绪。
一、过去的研究综述(一)人口历史学家:定期避孕来限制家庭人口?李中清与王丰认为中国传统生育制度的特色是通过“晚生、早停、生育间隔长”来有意识地、有目的地限制生育他们认为生育制度的关键是“婚姻内抑制”(即减少行房事的频率)来促成婚内低生育。
但是他们也指出了“一系列传统的生殖技术也有助于婚姻抑制”,包括“用各种中草药避孕,以及一系列流产技术”,同时通过溺婴和故意的忽略来除掉多余的孩子事实上,他们一定要通过所谓的普遍控制生育,来使他们所估计的生育率合理化,即比起大多数学者所提出的生育率要低得多,特别是当早婚对中国妇女来说几乎是普遍的情况。
李中清和王丰公开宣布的观点,来自于这些主要从人口记录中收集的定量证据(quantitative data),但是他们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却引发极大争议如武雅士(ArthurWolf)和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 以及其他学者所证明的,李中清与王丰的分析有漏洞的原因,首先是他们混淆了总合生育率(total fertility)与已婚女性的生育率(marital fertility);其次是包括了清代皇室贵族在内(但是他们是满族而非汉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都市精英);最后是他们使用了被下放在东北的旗人的不完整的数据,这些旗人有强烈动机避免自己被清政府计算在内;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武雅士和Engelen表明,最可靠的证据显示的是,传统中国生育率实际上与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生育标准是一致的:这一发现并没有证明中国人没有采用有目的节育来抑制人口,而是极大增加了李、王二人所必须给出的证据的负担。
他们必须或者将他们的论点扩大来包括大多数有着早婚和几近普遍婚姻的历史上的社会,或者给出原因为什么中国非用节育方法不可,才能获得其他社会能自然获得的生育率武雅士和Engelen使用台湾的户口注册(传统中国最精确的人口记录)来检验李王二人的观点:
关于中国生育的已接受观点是,大多数夫妇并不曾试图控制过生育,因为儿子越多越好这预测了一个妇女曾经生过越多的孩子,今后也可以生更多的孩子,因为她的生育历史表征着她的繁殖力李王二人的观点是,既然大多数夫妇只要一定数量的儿子,他们会控制生育的间隔时间,但并不会做的过度。
他们的观点预测了过去的生育与将来的生育的关系应该是相反的:换句话说,如果夫妻年轻的时候生育太多,那么他们应该尽量地抑制将来的生育率;而如果年轻的时候生育太少,那么它们将来应该尽量地多生几个孩子台湾的数据证实了已接受的观点:整体的模式是夫妇尽可能有很多孩子,而并非在达到某一高峰值时停止,任何限制都似乎来自于自然因素。
武雅士和Engelen得出的结论是即使真的有节育的实践,也并未在人口方面产生相当的影响本文将主要关注质性证据资料,因为任何来自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数据资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质性数据的支持,都应该有可疑之处。
正如武雅士所言,“如果真有他们所构想的那么多节育行为的话,就正如一只在客厅中的大象,它存在的证据将无处不在”但是王李二人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质性证据他们的方法只是声称他们的数据证实了节育的实践,继而推测要采取什么形式的节育措施。
例如,关于“婚姻内抑制”,他们引用了一种晦涩的文本传统,即提倡节制性交有益男性健康和长寿,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关于这些提倡抑制来限制家庭规模的文本的例子,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一文字记载的传统是否反映或影响了实际行为。
他们认为中国人使用了“一系列流产技术”又会怎么样呢?就具体的实践而言,李中清和王丰引用了《本草纲目》中列出的堕胎药以及李伯重关于江南地区控制生育的文章关于中国社会所谓普遍存在的堕胎,他们则引用了费孝通的话:。
根据中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的研究,到20世纪初,流产不仅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和使用,而且一个不知道如何用流产来终止生育的妇女,会被同村的人嘲笑为“笨老婆”考虑到费孝通的声誉,这段论述似乎可以被看成是有力的证据。
但是如果认真检查一下费孝通实际所写的,就会发现情况其实根本不同无论意义何在,“笨老婆”的轶事并非来自“一些地方”而是来自广西中部的大瑶山地区——文中所提到的人也并非汉族,而是瑶族的一支费孝通本人就他的发现所涉及的具体环境阐释得相当清楚,所以王李二人以此来暗示费所讲的是中国的一般情况实际上是在误导。
那么,费孝通是怎样认为中国人的堕胎行为呢?他确实在两本书中提到过中国人的堕胎,但是我无法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任何关于堕胎技术及其有效性和实际的发生率的的证据在他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费孝通附带地提到堕胎,但并没有涉及任何具体方面。
在他的理论研究论著《生育制度》中,费孝通列举了堕胎、溺婴和疏忽作为其他限制家庭规模的手段,引用了关于世界其它不同地方情况的已发表著作(例如马林诺斯基关于大洋洲特罗布里恩群岛的著名研究)以及他在田野调查中搜集的民间轶事(包括瑶族)。
费孝通对中国的讨论关注的是溺婴和疏忽,他并没有提到任何与堕胎实践有关的具体内容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费孝通确实非常简短地提到民间避孕法,“归有光母亲所吃的螺蛳,江村妇女所吃的鱼鸟蛋一类的东西,我相信是极普通的”。
费孝通并没有提供出处或更多信息但是“鱼鸟蛋”却让人想起上海妓女过去常吞食蝌蚪来避免或人工流产1958年,在经过严格检验后,蝌蚪已经“被官方宣布无任何避孕功效”一项研究显示,40%以上的参加调查的妇女在四个月内都怀孕了。
至于明代文人归有光,费孝通所指的应该是归有光写的关于母亲的小品文他的母亲16虚岁嫁给其父,随后生了七个孩子,婚后仅过了一年,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在终于给第七个孩子断奶后,她向女仆们抱怨自己已经因生育而筋疲力尽。
所以其中有人给了她两个“螺”,并用水服下,据说可以降低怀孕的频率根据归有光的记述,吃完这两个螺后,他的母亲就不能讲话了,不久就去世了,死时只有26岁明显的是,这个轶事并不包括有效避孕的证据,更别说“婚姻内抑制”了。
如果归有光的母亲真的可以得到安全的避孕方式,她也许会活得久一些总而言之,费孝通的著作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李王二人关于有效避孕和堕胎的观点其他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又怎么样呢?一些论述确实与这个问题有些关系。
例如,四川的老年妇女们告诉人类学家葛希芝(Hill Gates),她们年轻的时候所知道的关于避孕和堕胎的方法其实并没有用Elizabeth Johnson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她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堕胎在香港被禁止时)采访了香港新界的农村妇女。
她在记述中说,“没有任何妇女将禁欲视为是节育的一种方法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关于避孕,她这样说:“在现代控制方法被介绍之前明显缺乏有效的避孕方式接受采访者说或者妇女以前并没有避孕的方法,或者她们从没有听说过。
一位年长的妇女声称她在生育了十二次之后成功地避孕,因为她每晚临睡前服用一杯生盐水”但是,其他一些妇女确实试图堕胎Johnson采访了两个试图用传统方式堕胎的妇女,总共进行三次,似乎成功率三次中只有一次:。
一名中年妇女试图用从中药铺里买来的药堕胎,却没有成功另外一位(45岁)试图在第五次怀孕的时候堕胎,吃了各种药,甚至故意重摔了一次,都没有成功她第六次怀孕时堕胎成功了,因为她在第四个月的时候吃了一种中药既然至少有15%确认的怀孕自动流产(而且营养不良、疾病、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增加流产率),所以是否堕胎药在第三次尝试的时候有效并不能保证。
Johnson 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她的接受采访者反对堕胎,原因是“伤害妇女”:没有人在道德方面有异议;在这个阶段摘除一个生命并不会被视为是不道德的几乎所有妇女都这样说,堕胎不可取,因为对母亲的健康有危害……对健康的损害是最大的顾虑。
妇女用谚语来表达这种民间智慧:“宁生三子,不堕一胎”以及堕胎“如摘青木瓜,伤及树木,等成熟后摘取更好”总而言之,前述观点认为避孕和堕胎的传统技术安全、可靠,并被广泛而经常地使用,但Johnson的接受采访者所持观点明显与之不同。
堕胎会被偶尔使用,有时也许会奏效,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想象这些妇女会随便进行堕胎在就现代节育方式介绍之前的生活采访浙江萧山地区年老的农村妇女时,人类学家韩华(Hua Han)的一项新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观点。
韩华强调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生育基本上是没有进行控制的”,但是他的接受采访者报告了一些民间方法,至少一些妇女“使用它们来试图减少后代的数量,以减少抚养孩子所带来的身体上和经济上的负担”她们这样做并非是出于控制生育的集体家庭策略来提高家庭繁荣(如王、李二人所想象的),而是绝望的个人所秘密采取的措施,是违抗丈夫与公婆意志的。
而且,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方法起作用,韩华将它们描述为“常常冒险、危险而且无效的”韩华的接受采访者提到了三种据称可以防止怀孕或导致不育的草药,但是,“虽然许多妇女好像听说过这些植物和它们所谓的功效,却很少使用它们。
” 90位接受采访的妇女中只有一位曾经吃过其中的一种草药“河马子”“因为她的丈夫非常懒惰,几乎很少工作,所以她觉得在抚养现有孩子的同时再生一个孩子对自己来说太辛苦在没有告诉丈夫的前提下,她采草药,煮后定期服用。
”这种草药也许起了作用,因为她没有再怀上孩子(之前已经生了五个)但是韩华的接受采访者所表达的一致观点是,“河马子通常并没有效果,且有毒,特别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服用的话就很危险”另外两个妇女已经吃了大量的荸荠,希望可以避孕,但是并无成功迹象:其中的一个已经整整生了六个孩子,生最后一个孩子时已经37岁;另外的一个总共怀孕八次(包括流产一次),生最后一个孩子时已经39岁了。
这些数字显示荸荠大概没有什么避孕作用韩华的接受采访者所知的唯一堕胎方法就是自我伤害,使用织布机的水平捶打棍来敲打腹部这样的方法非常危险,且不可靠:正如韩华所言,“残酷,但并没有效果”一位曾生育了9个孩子的“模范母亲”(“因为无法得到有效的避孕措施”)报告说织布机的方法“也几乎没有作用。
”虽然许多妇女听说过使用织布机来堕胎的尝试,但是韩华只发现三个实际做过的人其中两个人报告说她们失败了,而第三个人相信她已成功堕胎了两次但是她一共怀孕15次,包括13次活产以及两次归因于织布机的流产十五次中成功两次,成功率只是13.3%,并在自动流产率的范围之内,所以她的例子也无法解释用织布机来堕胎的成功。
一个报告使用织布机没有效果的妇女解释说,“她不想要10个孩子,但是别无选择,因为那时在乡里或者镇上都没有有效的避孕方法”综述可见,韩华记录了因为身体不适和经济上的艰苦诸原因,贫苦的农村妇女渴望能够避免生育更多孩子。
既然至少有一些人因为有此愿望而行动起来,她们可以说是有主观能动性来努力控制生育但是韩华的研究也同时显示,这样的努力既不普遍也基本上是无效的李中清与王丰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引述了李伯重的观点,而李伯重将他们所说的清代中国妇女“采取了某些方法来控制生育”的观点接受为“事实”,并进一步解释她们是怎样做的。
李伯重认为,中国从宋朝到清朝期间防止或终止怀孕的技术“不断改进”,并“超过了近代以前的西欧”, 同时“这些生育控制方法的使用在江浙日益普遍,已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他所关注的是江南地区,但是声称这一地区“代表”这更广的潮流。
李伯重将这一关于进步的叙事部分地建立在一些从宋代到晚清的医学文本基础之上,他注意到,在这些文字记录中,堕胎剂的数量随时间而下降,晚期一些资料警告早期所列出的某些成分有毒他指出在一些较古老的文本中(如《本草纲目》)列出的成分经试验显示有堕胎的功效,但是其他的一些抑或危险(例如斑蝥)抑或没有效果(例如驴马肉)。
既然后期文本列出的可疑成分较少,所以李伯重认为这些技术一定是提高了,人们控制生育的效果也提高了他也引用了传统药典中描述的混有很多有堕胎功效的物质的详细处方既然单独使用时这些个别成分都有效(虽然这点并无确实证据),他就认为他们混合使用一定提高了功效,这样的用法可以被看作是随着时间而不断进步的有力证据。
但是,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同时使用多种草药只是一种鸟枪法,反映的是对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成分的怀疑这里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李伯重对医学文本的选择是很武断的他所选择列出的可疑堕胎药随着时间不断减少,这也许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观点并无实际意义,因为如《本草纲目》这类旧的经典一直在翻印,并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其权威性在今天的中医杂志中,涉及具体药物的文章基本上都要从引用《本草纲目》之类的经典药典开始,专治于不良反应问题的医师谴责依据古典医书“盲目用药”的普遍情况。
例如,2004年贵州一家医院治疗了73例中药中毒病症,在他们的急救报告中(包括五位使用斑蝥来自行堕胎的妇女),作者们观察到了这些情况:医者治病用药,总以《本草》为依据,而《本草》年代久远,不免有记载缺漏、记载不详,甚至误载的情况。
如用斑蝥堕胎和治疗狂犬病并没有得到实验或临床证实,却因《本草》记载而沿用至今,导致屡屡发生不良反应这些作者列出了其他几种选自经典药典的处方的实例,近些年导致了伤病、目盲甚至死亡的症状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将讨论近年来所持续使用危险性堕胎药的问题,包括被李伯重称赞作为进步的证据的那些消失于那些医学文本中的堕胎剂。
但是同样的,并不难发现一些晚清的医药著作,其中提供了现在看起来是可疑甚至是有危险的建议例如,所有官方仵作使用的法医经典《洗冤录》的晚清注疏中这样解释,斑蝥(其中含有剧毒的斑蝥素)是治疗狂犬病的有效成分,因为它有堕胎的功效。
据说原因是患狂犬病的狗可以使被咬伤的人怀很多微小的狗胎,如果长大就会让被咬伤的人死亡如果吃了与斑蝥蒸在一起的鸡蛋中,就会使狗胎以血块的形式在尿里排出来病人必须继续服用搀有斑蝥的鸡蛋,直到没有血块出现根据这个文本,这种疗法是“以毒攻毒”的范例。
(斑蝥素可以导致肾衰竭,这大概就是有血块出现的真正原因)有意思的是,同样的法医手册的晚清注疏也提供了斑蝥中毒的解毒药方但是这一药方也包括猪膏;而今天的毒理学家警告说,富含脂肪的食物会加速斑蝥素(斑蝥中的活性剂)的吸收,所以任何有斑蝥中毒症状的人应该严格避免食用。
因此,看起来很可能是《洗冤录》的晚清注疏中说的解毒素实际上加速了斑蝥中毒的致命性这些例子所显示的是,更广泛地阅读医学文本就会发现李伯重所相信的进步论并不能得到认可但是李伯重使用的证据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他所引用的药典显示出其精英作者也许。
相信这些药有堕胎或避孕的功效,但是它们并没能证实这些药是否实际产生作用,或者到底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一点很关键:一些人肯定相信(甚至到现在还有人继续相信)一种或另一种疗法可以进行堕胎或避孕,例如蝌蚪、螺、斑蝥、盐水、荸荠等等。
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并不能作为证明有效的证据李伯重认为现代实验已经证明某些讨论的传统药物有真正的堕胎和避孕功能,但是正如 Gigi Santow 所指出的,实验结果和临床试验并不能复制这些药物在过去的时代被使用的真实的生活情境,它们经常试验材料中提取的化学成分并开出精确剂量(这在传统的药物准备中是不可能的)。
而且,试验显示许多用来避孕或堕胎的传统材料(例如蝌蚪)并没有任何治疗的价值李伯重承认他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这些方法怎样在实际中被广泛使用的实际依据但是这一不便的事实并没有阻止他做出这样的推论——其观点建立在种种来自小说和文人笔记的轶事基础上——到明清时期,堕胎实践在整个江南地区已经“十分普遍”,堕胎的服务也“十分容易获得”。
到那时起,“主要节育药物,大多数都是常见药物,价格也不甚昂贵”对于避孕和不育他也有相似的观点,同时强调“至于堕胎药物,则已逐渐变得比较成熟,因此运用亦较广”;总而言之,“传统的控制生育方法变得非常流行而普遍。
”李伯重得出结论,“因此那种认为近代以前的江浙人民的人口行为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行为的设想,肯定是不符历史真实的”但是这一结论是建立在臆测基础而非坚实的证据上堕胎和避孕看起来不太可能在整体上对人口方面产生明显的影响。
但是这一结论并不一定排除掉性别历史学家所声称的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精英女性终止怀孕的情况她们又是提供怎样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观点呢?(二)性别历史学家:精英女性所采取的自主的生育控制?两位卓越的性别历史学家白馥兰(Bray,1995、1997)和费侠莉(Furth, 1986、1999)都使用男性文人医师的文字记载,来研究帝制晚期中国精英阶层女性的生育控制。
正如白馥兰和费侠莉所阐明的,这些医师将堕胎视为一种冒险性的措施,只有在紧急情况才可以实行:他们都一直警告堕胎药是有危险的,并讲述服用如牛膝、麝香、肉桂这些通行的药物来堕胎所导致的病症和死亡的案例,进一步加以警告。
但是,如果一位妇女的生命处于岌岌可危,医师就会开堕胎的处方来试图救她:无可置疑的是,他们认为母亲的生命要比腹中胎儿的生命更重要尽管如此,白馥兰和费侠莉也坚持认为“通经药”使精英女性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自己的生育。
当一位妇女的经期来迟,这些强度大的药可以用来“疏通”月经;男性医师在这方面一起合作,因为他们都认为月经有规律是女性健康和生育的关键而且,堕胎药中相同的一些成分也常用于通经药因此,白馥兰和费侠莉都认为这些精英妇女可以利用这种含糊性来中止不需要的怀孕:事实上,怀孕早期被委婉称为“月经不通”,用委婉称为通经药的堕胎药来“治疗”。
模糊性是关键,因为看起来没有人会明确承认这种疗法其实是堕胎在我看来,这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她们关于精英女性使用堕胎药进行生育控制的观点与她们的资料中关于堕胎危险的明确警告,这两方面是相冲突的但是白馥兰和费侠莉从来没有解决这其中的矛盾。
其二,关于妇女是否实际上以他们所指出的方式中止不需要的妊娠,她们并没有提供任何有记录的事例出于获得灵感的考虑,白馥兰和费侠莉都引用了人类学家 Chor-Swang Ngin 的田野调查,即在马来西亚的有华裔妇女所使用的调节月经的民间方法;白馥兰也引用了采访哥伦比亚妇女的人类学家 Carole Browner 的类似发现。
Browner 注意到哥伦比亚妇女“利用这种孕期开始的模糊性”来“调节生育”:妇女们创造了时间上的间歇,即在怀孕后但在承担孕妇职责之前,于是在这期间她们进行生育控制这允许他们中断不想要的妊娠,同时逃避处罚,包括她们将自己与堕胎联系在一起的悔恨。
Ngin 也有相似的解释:当一个发展中的胎儿变成人形时,消失的月经与肯定怀孕之间的时期成为民间信仰中的模糊时期,其中恢复月经的手段不能诉诸于法律处罚或被在医学上被定为堕胎白馥兰和费侠莉将这一观点应用于中国:一个20世纪晚期马来西亚和哥伦比亚的穷苦妇女的民间疗法,被毫无痕迹地转化为帝制晚期中国精英阶层妇女的堕胎实践,这一转折暗示着相同的逻辑在三种不同环境情况中起作用。
费侠莉引用了Ngin的博士论文,发现“调经疗法强调的是生育能力和繁育,但是如果一位妇女不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这样的治疗会隐藏堕胎的企图”换言之,“‘月经调节’的流行归因于对于妇女身体内在状况的模糊性”,以至于“堕胎的欲望可以秘而不宣,并因此不受指责。
”在从费侠莉处引用了这一段后,白馥兰这样总结:我想要再进一步的强调……医学文本显示的是正统的妇科学为明清时期精英阶层的妇女提供了一种众所公认的生育控制技术,所提供的当然不是全部的生育自由而是调整的策略空间,以及培养社会母亲
(social mother)角色的可能,同时也可以避免带有生育负担的生理母亲(biological mother)的职责白馥兰更大的论点是一个精英阶层的妻子将要进行节育(使用的委婉说法是用月经调节来掩饰中止不需要的怀孕)以此来促进劳动分工,在其中她可以垄断社会母亲(social mother)角色的权威和特权,同时将一些生理母亲(biologicalmother)角色承担的义务和风险转嫁到家中处于次等地位与其夫可发生性关系的妇女身上(即妾与婢女)。
换言之,“生育操纵的灵活性被限制在地位高的女性身上,依靠的是大家庭中女性内部等级的不平等造成的剥削”但是,要想成功,这种剥削式的劳动分工应该取决于一位精英阶层的妻子实际上避免生育的能力——亦即假定的是这种“生育控制技术”实际上起作用,且足够安全进行常规使用。
否则,这能提供多大“调整的策略空间”?但是白馥兰回避了功效的问题,她没有提供多少相关证据,而且她所提供的少量证据并不能让人相信这些堕胎药实在可靠她和费侠莉都很重视一位十七世纪的医生程茂先所记载的情节,其中程记载了他治疗自己妻子的一次艰难的怀孕。
她的健康在多次艰难的怀孕中已经被严重损坏,在40岁时,她的月经停止了因为害怕再次怀孕带来危险,所以程开出“通经药”,但是没有效果白馥兰将这种情形称之为“一个‘可能性怀孕’的典型事例”,并且将程夫人使用通经药比作Browner所采访的哥伦比亚妇女模糊性的自我药疗。
相反的是,我将之称为一个典型的医疗紧急事故中诉诸于堕胎的事例:原文无疑问地表示这是终止怀孕的一种尝试几个月后,程的妻子开始出血,他以为她也许会流产程相信“若果小产不幸而幸”,试图给妻子“破血药”来打胎 。
但是第二次实验也失败了,她活了下来,并最终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婴程将这一结果归因于命运:这个男孩注定要诞生,任何都无法阻止但是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是:程的妻子被迫怀孕到足月,是因为这些药并不起作用而且,她之前多次怀孕耗尽精力,这表明了有效节育相反的一面;她使我们想起了归有光精疲力竭的母亲,在整个短短的婚姻生活中不断被奴役般怀上孩子。
在评价程的妻子的故事时,费侠莉明确承认这一点:“这个情节让我们知道,调经药和破血药如果作为堕胎药不但危险而且不可靠”但是不论费侠莉还是白馥兰都没有试图用这一结论来调和她们的观点,即精英阶层妻子通过使用通经药而终止不需要的怀孕并以此获得生育的“调整的策略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 Carole Browner 或者 Chor-Swang Ngin 都并没有说他们的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的接受采访者所使用的民间疗法实际上真的很有效相反的是,这两位学者关注的是使用这些疗法的妇女“以为它们有的属性”(perceived attributes)因而可以理解这些妇女的精神状态——尽管可以获得那些更加可靠的现代疗法,她们还是继续采用这些民间疗法。
Browner和Ngin的证据显示出民间疗法在避孕和中止怀孕方面远远不是有效的事实上,这两位学者研究的动机之一是发展更有效的机制,让更多人可以接受现代避孕措施在帝制晚期的中国,一些精英阶层的妇女利用月经调节的模糊性来中止不希望的怀孕,作为一种形式的生育控制
也许是真的也许财富使她们有机会接触到技艺精湛的医师,可以将这些药物的风险程度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所以可以进行有选择的堕胎但是白馥兰和费侠莉并未提供任何清楚的证据,即任何人真正在这样做没有这样的证据,她们的观点仅停留在推测的层面。
而且,有充分的原因让我们怀疑正如白馥兰所指出的,其中一些过去用来“通经”的药物也可用来“破血”或“打胎”,在“通经药”的种类中当然有模糊之处正如我们所见,程茂先的妻子第一次试图堕胎时服用了程所称的“通经药”,而且在现代台湾,“通经”和“调经”这两个词有时都是对堕胎服务的委婉说法。
尽管如此,月经调节与堕胎之间到底存在着多大的模糊性并不清楚剂量大概会有变化,取决于使用这些药物的目的但是白馥兰和费侠莉几乎没有提及剂量白馥兰在脚注中提到18世纪医师徐大椿所记载的案例:另外一个医生用来打胎的牛膝根的剂量是比常规的剂量。
大30倍到50倍,以至于孕妇最后死于大出血这一轶事似乎证实了当用作是堕胎药而不是简单的通经药时,同样的药物大概会以不同方式使用而且不清楚的是这样的药会怎样随便被使用:一些医学权威认为,除非在非常必需的情况下,这样烈性的药物应该被避免使用。
例如,正如白馥兰自己指出的,徐大椿警告不要使用通经药来治疗月经不调,因为太危险,“乃命止药”研究精英阶层妻子的生育率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低于他们丈夫的妾的生育率将会很有意思如果白馥兰是正确的,我们会期待妻子的生育数量一直比妾要少。
不过,即使这样的差别存在可以建立起来,也不一定是因为妻子使用堕胎药纳妾的标准借口(也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正统的说法)就是妻子不育但是即使妻子是可以生育的,这种生育率的差别也许只是反映了丈夫比较偏向于与妾有性生活(丈夫与妻子的婚姻是包办的,而选妾却是出于丈夫自己的喜好)。
白馥兰更大的论题是在一夫多妻制大家庭中妇女之间的劳动分工,就是说将“母亲”的角色里面的社会性方面与生理性方面分开来让不同身份的妇女(妻、妾、婢女)来承担我也认为这个论题非常可信,但是这并不要求妻子使用药物节育。
毕竟,白馥兰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展示一夫多妻制可以怎样服务于精英妻子的利益,正如她自己所指出的,有许多记载的实例是关于妻子为丈夫纳妾的帝制晚期的男性作者将这种行为看成是模范式的自我克制,其中妻子为了丈夫的舒适压制自己天然的嫉妒——但是这种解释所假定的是妻子希望与丈夫同房。
如果一个妻子真的想要避免自己角色的生理责任,有什么方式比给她丈夫提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更好的呢?这一简单的快捷方式比起自己服用有毒的药物更加可取
二、清代法律中关于堕胎的记载从上述讨论可见,人口历史学家和性别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可靠的质性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能提供明确的、有记载的实例,即关于任何人实际用堕胎(或任何其它方式)来进行常规的生育控制,或者限制家庭规模,或者避免妻子/母亲的角色所应承担的生理责任。
尽管如此,重要的问题仍然存在谁会实际上试图堕胎,并且在什么情况下呢?也许用来调查这个问题的最丰富的未利用资源是清代的法律案件记录,其中有时会记录一些堕胎的尝试但是要想理解这一证据,我们需要深刻了解官方在执行法律是怎样理解堕胎的。
(一)清代法律中的堕胎过去,对中国堕胎历史感兴趣的美国学者基本上从清代法律中调查堕胎“合法”与否这一探寻的思路,可以追溯到Bernard Luk的一篇重要文章他在文中发现《大清律例》中并不含有明确的全面禁止堕胎的规定。
但是Luk进一步将缺乏这种规定描述为“传统中国堕胎的自由”,这可以给一个中国妇女“比起其西方妇女姐妹们大得多的自由来除掉子宫所含之物”后继学者也倾向于援引Luk误导性的观念“自由”例如,白馥兰将 Luk作为她唯一的参考资料,并走得更远,她将这一明确的法律权利归因于清朝的个别妇女 (这是Luk自己所不曾做的):“一位妇女在等级制度上位于孩子(不管是出生的还是未生的)之上,所以她的生命更加珍贵,所以她处理掉自己孩子的权利在法律上予以承认。
”事实上,没有任何朝代的法律承认这样一种“权利”这一思路的参考框架是现代美国关于堕胎的争议在美国,堕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关于政府应该起什么样作用来实现个人权利的问题:是应该保护一位妇女的“选择的权利”,还是胎儿“生命的权利”?然而,将这一参考框架应用于清代法律却是毫无意义的,其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权利的观念,没有任何一个词表示这一概念,而且,清代法律在原则上并不承认其在涉及皇帝的臣民的生活范畴方面是有任何限制的。
只有暂不考虑权利这个时代错误的框架,我们才可以理解堕胎在清代法律中的地位明清时期的医学文本将堕胎描述成因医疗危机而采取的正当的冒险性措施,清代法律文本将堕胎描述成因通奸怀孕这种社会性危机而导致的绝望且有着潜在致命性的行为。
就我所知,堕胎仅仅在此种语境下才在清代公堂上出现例如,有时候因通奸怀孕的妇女尽管成功堕胎后奸情依旧泄露,在此种情况下奸夫、奸妇会因非法关系被告官但是,出现在档案中的大多数情况中,一位妇女因通奸而怀孕试图依靠堕胎来掩饰,服用堕胎药反而让她致死。
在这种情况下,控告的对象就成为提供这种致命的堕胎药的人关键文本是1740年的一条新例,见《大清律例》中的一章“因奸而威逼人致死”:妇人因奸有孕,畏人知觉,与奸夫商谋用药打胎,以致堕胎身死者,奸夫比照‘以毒药杀人知情卖药者,至死减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若有服制名分,本罪重于流者,仍照本律从重科断如奸妇自倩他人买药,奸夫果不知情,止科奸罪清朝时期一条新例的颁布,典型性地回应了省府官员的要求,他们遇到了《大清律例》并没有清楚涵盖的特殊的案件颁布1740年的新例,表明地方执政官需要审判相当多数量的符合这一情况的案件。
一位乾隆朝的资深官员吴坛这样说,“惟因例无明文,是以各省办理颇不画一,乾隆五年(1740年)馆修,将酌纂例款,以便引用”1740年之前处理这种案例的一种方式可以在1737年的一桩案例中看到, 一个男人在提供了堕胎药给与他通奸的女人后使得女人中毒致死,这个男人因此比照基本的(而并不详细的)“因奸威逼人致死”律,被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吴坛评论道,“若照‘因奸威逼人致死’律将奸夫拟断,则事起和奸本非‘威逼’”,因此处罚会太重;但是,“如仅止科奸罪,则死实因奸而致”,因此处罚会太轻所以,1740年的新例取得了平衡此条例文敏锐地意识到通奸也许会是导致堕胎的原因,而且,堕胎的企图很可能是致命的。
为了决定适当的惩罚而比照的律文,强调的是堕胎的明显危险:一副堕胎药类似于致命的毒药(对妇女来说是致命的),一个提供了可以将妇女致死的堕胎药的男人,等同于提供工具来故意挑唆谋杀的人其中的含义是,此男应该已经知道
打胎的尝试有致死的危险吴坛这样解释道:堕胎之药,性皆酷烈,受其攻逼,十无一生在奸妇虽孽由自作,而奸夫既隳其节,又戕其命,未便竟从宽典也许是为了修辞的效果进行夸张,吴坛指出死亡率超过90%尽管如此,他的关于堕胎药存在潜在致命性的基本观点,与可获得的其余证据是一致的。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资深官员,吴应该知道自己在讲什么1740年的例文阐述的仅仅是奸夫为与其通奸者找到一幅堕胎药,从而导致了她的死亡;但是医师、草药师以及接生婆这些在这一情况下提供了堕胎药的人也将被严厉惩罚。
案例记录显示了应该援引几种不同的法律来审判这些人,看起来并没有绝对一致的政策例如,《大清律例》中的“斗殴”律包含这样一则条款: “折人肋、眇人两目、堕人胎、及刃伤人者,杖八十,徒二年”在一个 1767年的案例中,这一条律被引用来宣判一位向通奸者提供了致命的堕胎药的医师。
在其它情况下,我们发现1740 年的例文也出于此目的被援引,提供堕胎药的医师接受的审判被降了一级,作为“为从”(与“为首“相对,亦即奸夫)在19世纪早期,审判人员解决一项政策,将为奸妇提供致命的堕胎药的人比照《大清律例》中“诈伪”一门中的一条律。
这条律惩罚各种声称诈病来避免官方责任的人,包括为了逃避审讯与惩罚而故意造成自我伤害的刑事被告人它增加了以下这一条:其受雇倩为人伤残者,与犯人同罪因而致死者,减斗杀罪一等这种比照后面的逻辑是一个因通奸而致怀孕的女人是一个“犯人”。
用打胎来隐藏通奸,被视为一种逃避惩罚的企图因此,售与她堕胎药的医师或者草药师,事实上接受钱款作为交换来伤害她并怂恿她逃避惩罚因此,如果堕胎药导致奸妇致死,那么这条律的最后一句子应该可以适用: 最终的处罚是“杖100流3000里”。
那就是1740年例施加于提供了致命的堕胎药的奸夫身上同样的处罚这种在处罚上的平等明显是有意为此这种类比再次强调的是对高风险率的明显了解:从打胎到自残,卖出一副打胎药等于是在获利的同时伤害他人这一感知在清朝版本的官方法医学著作《洗冤录》中进一步加强。
这些文本包括对摄入堕胎药而致死的女性尸体的描述,以及明白怎样确定这些案例中的死因例如,一个版本描述了一具江西乐安县的女尸,是一位妇女在1794年咽下了混有麝香与红花的堕胎药后死于大出血这些法医手册也开出了治斑蝥和芫青(青娘虫)的解毒药;这两种有毒的昆虫都被认为有堕胎的功效,在清代(一直到现在)尝试堕胎是中毒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考虑“权利”的问题,我们会发现清代的成文法和司法档案中将堕胎描述成一种因通奸而致怀孕的妇女所尝试的绝望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行为清代法律首要考虑的并不是禁止堕胎本身,而是要惩罚通奸双方,也包括那些怂恿尝试打胎且最终导致通奸女方死亡的其他人。
但是,我要补充的是,我并未发现清代的法律资料中提及在通奸情况之外的堕胎行为是常见的,甚至是社会上或者法律上可以接受的(二)清代案例中的堕胎行为在清代司法档案中我已经见到了涉及堕胎的许多案例我并没有先见之明来复印所有这些材料,但是我收集了自认为有代表性的26个案件样本。
我也用官箴、判牍中总结的其他五个案例来补充这些档案中的26个案例这31个案例样本,包括24个完整的堕胎尝试和3个不完整的尝试 (其中妇女的行为被中断并被阻止继续下去),以及4个妇女积极寻找堕胎方法但是并没有找到的案例。
使用法律案例来评估社会实践,存在的明显问题是其所记录的都是处于事故或陷入困境的人们我在清代法律资料中见到的所有堕胎企图包含的是因为非法性关系而致怀孕的妇女,至少这些企图中的三分之二导致了最终的死亡如果这是真的,即许多已婚妇女经常安全地打胎并将之作为可以接受的日常节育制度的一部分,她们大概不会出现在法律案例的记录中。
但是这种假想存在的问题是她们看上去也并未出现在其他任何资料中很难认同一种广泛的社会实践却并没有任何记载的实例这些法律案件的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其确实提供了27个有记录的具体例子,即关于打胎在事实上的尝试,有一些甚至非常详细,显示出社会语境、使用的方法及其后果。
它们尤其牵涉了普通妇女,而不是明清医学文本中聚焦的精英阶层的妻子我认为这一样本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偏颇——比如,不论结果如何,大多数尝试的堕胎行为应该从未报告给官方即使如此,清代的法律案件似乎提供了关于堕胎行为在帝制晚期中国的。
唯一有记载的具体例子,除了白馥兰与费侠莉所引用的医学文本(这看起来并不能支持她们的论点)而且,许多其它案例并不包含堕胎的尝试,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解释堕胎(以及节育这个大的方面)的易得与否——这一证据证实甚至对于那些想要堕胎的妇女也不必然能得到。
来自法律案例的证据也许并未估计到肯定的结论但是,任何关于在帝制晚期中国堕胎的理论至少应该可以解释这一证据下面这一览表显示的是我的案例样本中的31个妇女的婚姻状况,她们都试图或积极地想要堕胎31个试图或积极想要堕胎的妇女的婚姻状况。
寡妇中的一个做过妓女,她在这个样本中很独特是因为她所关心的是自身生计而非掩盖自己的性关系——她害怕怀孕会影响她的生计其他的30个妇女都绝望地想要堕胎,因为她们害怕将自己婚外性活动暴露后的结果为什么她们这样恐惧呢?。
我们不应该假定这些妇女的家庭和社区也必然同意官方以及精英阶层对女性贞洁的坚持——有问题的是在什么程度上普通百姓从自身角度支持这些价值肯定的是,至少一些丈夫和公婆觉得有权处死通奸的媳妇,虽然从这些例子中常常可以体会到有别的隐蔽的动机。
但是,重要的是,在几乎所有这些堕胎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极大提高了牵涉人员的风险的具体因素,这给了她们焦虑的另外的原因,不仅仅是简单的出于丢脸的考虑(一些案例包括不止一个这样的因素)提高妇女因通奸而怀孕的风险的情况
独立的寡妇在这个表中很突出,不仅仅是因为她们也许比其他妇女有更多机会从事这类事件大多数寡妇在第一个丈夫死后出于必要原因迅速再婚,但是对于那些丈夫留下足够财产的寡妇而言,她们却大概不会再婚(除非她得到公婆的同意来招到一个入赘的丈夫)。
但是,重要的是,一个寡妇的独立(包括对丈夫财产的控制和对孩子的监护)取决于她在贞洁方面的名声如果她被抓住通奸,她的婆家就会有权收回她丈夫的财产和孩子,然后或者将她送回娘家,或者将她嫁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贞洁话语是在物质利益冲突时使用的一种武器。
第二个突出的因素是乱伦,通常包括妇女与她们丈夫的近亲发生性关系,一旦暴露,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和法律后果按照清代法律,妇女若与丈夫的兄弟、侄子、或叔舅之间(即使在清代中国娶兄弟的未亡人[转房婚]并非稀奇)发生性关系或结婚,双方要被处死。
在我的样本中的几个案件中,死刑最终被执行了如果妇女与丈夫家中的长期雇工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男方也可能会被判死刑,这一情况也出现在堕胎的案例中在牵涉到尼姑与和尚的案例中,事情败露导致双方都被强迫还俗,也因此失去了生计(再加上因非法性关系受到惩罚,而且这种惩罚对僧侣比一般的人更加严格)。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双方都急切地避免被泄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愿意冒着堕胎的巨大风险这些妇女们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尝试堕胎呢?她们有多么成功呢?在全部27例尝试中,有一例包括自我伤害,还有一例未知,但是所有25例用的方法是堕胎药。
10例列出了具体药物,还有几例明确解释了怎么使用这些药物中大多数都是口服使用,但是另外一些用作阴道栓剂或者腹部膏药例如,一个1850年的四川巴县档案的案例中牵涉到万县寡妇谭刘氏她在与死去的丈夫的一个亲戚谭焕达通奸后怀孕了。
在回娘家探亲时,她的父母注意到她隆起的腹部,指责她怀孕了她否认这一事实,但是绝望地要避免被公婆发现,于是向一位女草药师谭方氏倾诉,求一付堕胎药,并答应见效后付以重金谭方氏从房后摘了牛膝根一把(看来家中有园子),并解释怎么准备。
谭刘氏用水煮了牛膝,煎煮服下次日清晨,打下一个胎儿,她“将胎丢弃”但是却止不住血崩,五天后就死了临死前,她承认自己通奸、怀孕和堕胎这些事情,但是却拒绝说出谁是她的情人和提供药物的草药师几年后,谭刘氏之子从谭方氏处听说了发生的事,所以他谋杀了其母的情人谭焕达来为她报仇。
杀人罪是整个刑事案件的焦点考虑到这些情况,谭刘氏的儿子(杀手)只是受到已减轻很多的徒刑,在巴县服务因为提供了致命的堕胎药,谭方氏被判“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的是“其受雇倩为人伤残者,与犯人同罪因而致死者,减鬪杀罪一等”律。
但是最后因为特赦,她才得以免受刑罚我们已经知道了谭刘氏使用打胎的草药——牛膝,直到今天还在中药中广泛使用牛膝有堕胎功效是广为人知的,并且是这些制剂中(煎煮药和阴道栓剂)的常见成分:和许多这类草药一样,它可以导致子宫出血,除用来打胎之外,经典药典中推荐它来治疗月经不调,或取出残留的胎盘或者夭折的胎儿。
大剂量的牛膝是可以致死的谭刘氏的死并不特别:白馥兰和费侠莉所引用的医学文本也讲述了妇女死于服用大剂量的牛膝来打胎的例子浙江海宁县的一个案例,报告1793年,涉及寡妇徐祝氏, 她与身为和尚的夫弟履冰(45岁)发生性关系。
当这名寡妇意识到怀孕时,她告诉履冰“弄药打胎”根据她的儿子(他已经知道她的奸情但是不敢违抗母亲)的说法,在企图堕胎时她已经“肚子大”了后来履冰供说他刚开始拒绝去找堕胎药,但是她因此逼迫他,去了他的寺庙并拒绝离开直到他同意。
所以他只好去了一家药店买了三种药物:红娘子,麝香,山楂记录并没有显示他买了多少或者花了多少钱他煎了这些材料,让徐氏把煎剂服下结果是徐氏严重腹痛以及大出血,在36小时之后死去后来,地方官问履冰,“那堕胎的药方是那个传你的?”这个和尚供说,“ 小的向来听得人说红娘子、麝香是下胎的,故此去买的,并不是那个传授,也不是药铺里知情卖把小的的。
”这个和尚于是被判绞立决,因为与兄妻通奸,这甚至取代了购买堕胎药的罪毒死徐祝氏的药都是有名的传统药物山楂果可以用于多种情况,包括治疗闭经,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是红娘子(红娘虫)却有剧毒它的性质与斑蝥和芫青(青娘虫)相类似。
这三种昆虫都被列在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政府控制使用的有毒中药表中如果内服的话,这三种昆虫即使是小剂量服用也是致命的 (典型的死因是肾衰竭和内部化学烧伤)麝香是一种鹿的腺体分泌物,味道十分强烈,在中药中是用来堕胎的有名成分,但是如果内用也是危险,有时是致命的。
麝香又一次出现在来自江苏金匮县的一个案例中,报告于 1767年, 涉及一名叫朱氏(18岁)的童养媳,还没有与未婚夫陈幅郎 (17岁)成婚她与一个叫倪惟良(45岁)的鳏夫有染后怀孕倪从18岁起定期为陈家干活,每年的工资大概有银5、6两。
朱氏担心如果公婆发现了她的奸情后自己的生命会有危险倪告诉她“妇人身边佩戴麝香就可堕胎”,所以她给他钱300文去买麝香倪让他的表弟,一个名叫华群的医师去买一点麝香,告诉他自己“要做香袋用的”朱氏佩戴麝香六个星期后却没有效果。
倪越来越绝望,最终告诉他的表弟真相,并请求他开出堕胎药,说朱氏和他的“性命难保”华同意帮忙后,买了硼砂和樟脑,将它们与麝香混合,将混合物制成三个药丸,告诉倪如果朱氏“塞入阴户或可堕得胎下”记录中并没有给出这些成分的具体数量或者价格。
但是,当后来被质询时,华群坚持供说他“平日也不是惯代人家打胎的”朱氏依照华的说明行事,但是几天之后她高烧病倒,不仅腹痛剧烈且骨盆痛她疑心的婆婆闻到麝香的味道,于是盘问朱氏,她只好说出了一切陈家把朱氏的哥哥叫过来,她也向他坦白一切。
在随后的几天中,朱氏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所以她的哥哥将她带到倪家并将他留在那里(这意味着她的死将是倪的责任)同时,她的公公通知当地的总甲长,总甲长又将这桩丑闻报告给县衙门知县派信差去逮捕倪,并派了一个医师照料朱氏。
朱氏的病被诊治属于绝症,但是为了救她,医师还是开了药方来“安胎”尽管如此,第二天(在塞入栓剂十天之后)朱氏还是在排出腹中胎儿后死去了依“雇工人奸家长之期亲”律,倪“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对这一罪行的惩罚,取代了对求取致命的堕胎药的惩罚)。
华群给药堕胎,应照“斗殴”律中关于“堕人胎”的条款杖八十、徒二年某些经典文本提供了关于堕胎栓剂的处方,包括毒死朱氏的麝香常常与牛膝根一起使用我还没有找到其它的包含硼砂和樟脑的堕胎处方,但是樟脑是有剧毒的,而且和麝香一样,如果内用也很可能会致死。
我所见的清代法律案例肯定了其他资料中的信息,即药物是当时最常用的堕胎方式结果是令人沮丧的:24位完成堕胎尝试的妇女中,17人死了,幸存的7人中,确实有6人打胎成功,但是至少其中的2人受害于严重的副作用,患病数月(我们缺乏关于其他4人的详细信息,所以不知道她们受害与否)。
第7个幸存者的堕胎尝试失败了总而言之,在这个样本中,明显的成功率是四分之一(虽然至少15%承认的怀孕自动流产了,实际的成功率也许还要更低),相比较,致死率却是超过三分之二这一证据显示,传统打胎药物更可能导致疾病或死亡,而非安全打胎。
当然,我们必须要假定法律案例中会过分强调消极后果即使如此,这一证据帮助我们理解了医师徐大椿警告那些药物有毒因此“乃命止药”的段落,还有资深官员吴坛的发现“受其攻逼,十无一生”,以及人类学家Elizabeth Johnson的接受采访者的声明,传统打胎方法很危险以至于“宁生三子,不堕一胎”。
这些例子显示出堕胎是可能的这种普遍意识(我的样本代表了安徽、福建、广西、贵州、湖南、江苏、江西、山东、四川、云南、浙江和河北),但是也显示出有许多误会,同时也认为应用实际的堕胎方法需要一个相当专业的知识领域。
比方说,许多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麝香有堕胎的功效 (例如,是麝香的气味让朱氏的婆婆怀疑),但是他们并不一定知道怎样使用它来打胎,更别提安全使用它了例如,倪相信妇女可以通过简单闻麝香的味道就可以堕胎(这是持续至今的迷信),而当不起作用时,他和他的情人就不知所措了。
而且,几乎所有使用堕胎药的妇女都不得不从草药师、接生婆或医师处获得(在我的样本中只有一个例外的案例),同时要付相当多钱
(三)堕胎的费用及易得程度既然堕胎药通常必须要从有一定程度专业知识的人处购买,一个重要的因素来估计堕胎的易得程度是费用的问题堕胎的费用是多少呢?那时很多人可以负担得起吗?堕胎药中的成分一定在价格上起伏很大:一种普通的草药如牛膝也许曾经非常便宜(或者甚至是免费的,如果知道怎样找到的话),但是奇异药材如麝香、樟脑、桂皮以及水银大概要贵很多。
麝香是在我的案例样本中最常被提起的堕胎剂(在这十个案例中我们知道妇女使用的是什么药物,其中五个使用了麝香,并常常与其他药物一起使用)它长期以来被用作香水和中药中的珍贵成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案例中描述的堕胎药制剂中具体成分的数量,也不知道购买其中的大多数需要的确切价格。
例如,在上面所引述的最后一个案例中,倪惟良花了钱300文来买数量很少的麝香,当时价格可以与倪每年的收入银5、6两(差不多是钱4000文)相比较但是既然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倪买了多少麝香(更别提质量)或者是否华群需要更多来准备栓剂,所以不可能来估计价格。
(我们也不知道樟脑和硼砂的价格)既然麝香如此烈性,又如此昂贵,大概只使用了很少的数量一位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医学传教士记载的两个在华北地区使用的堕胎处方中显示了相当大的幅度:一副煎煮的口服药只包含0.37克的麝香,但是一个栓剂中却包含十倍的量——后者很可能是危险的,既然如果内用仅仅3克就可致命。
幸运的是,我们确实知道八个法律案例中堕胎的费用。八个法律案例中堕胎的费用以及地点和年代
要正确地看待这些价格:1.5 石米包含了大约一个人一年的供给;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农业劳动的年工一年的平均收入大约是钱3000-5000 文或者银 5-7 两,取决于支付的媒介有时候卖妻所得是相似的数额:例如,在一桩 1798年的云南永善县的案例中,一个男人迫于贫困卖妻(25岁,有生育能力的证明)只赚了五两银。
让我们具体看两个例子在一桩1773 年江苏金匮县(上述朱氏与倪惟良的案例发生的相同的县)的案例中,寡妇章杨氏(27岁) 与死去丈夫的侄儿章宝私通后怀孕了章的朋友潘永林与他的伯母潘张氏 (50岁的寡妇)住在一起, 潘张氏是稳婆。
章宝问潘是否他的伯母可以打胎,但是潘并不知道,所以带张去见她这个稳婆后来证实“从前并没有替人打过胎的”,但是她的婆婆很久以前告诉过她怎么做,所以她同意帮忙潘张氏将一小块麝香放在牛膝草的茎尾端,并用丝线扎结实;通过触摸她才意识到章杨氏已有5个月左右的身孕,所以她用一个长5寸(约16.5厘米)的茎,因为她的婆婆告诉她每怀孕一个月长度应该是一寸。
她就将这一装置“放入(章杨氏的)产门”,并将之留在那里;24小时以内,这个寡妇就大出血,流产后死亡考虑到茎管的长度,子宫壁也许被穿孔了这个稳婆同意提供堕胎,价钱是三两七折钱,等于钱2100文为了付款,章给潘章氏一石米(价值二两七折钱,等于钱1400文),余额用现金结算。
从这一信息中,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些费用的实价是1.5石米这个案例中牵涉的都是贫苦的农民,对他们来说这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款项在这些费用中,章宝首先预付给了稳婆0.4两七折钱(等于钱280文)用来买堕胎药的成分;在她插入堕胎装置后,他付给她米以及余额。
既然潘张氏自己摘了牛膝草(在附近的水稻田边),头款大约可以支付麝香的花费换言之,付给稳婆的超过五分之六的费用偿付了她关于用什么和怎样用的知识(看起来并不普遍的知识)以及她的谨慎保密如果我们接受了潘张氏的证词(当事的知县和他的上级也接受了),那么堕胎并不是她的稳婆实践中常规的一部分——事实上,她甚至从来没有尝试过。
也许她在说谎;也许,她实际上经常为已婚夫妇提供安全而有效的堕胎手段,将之作为节育的一部分,而这一案例中的致死只是一个偶然事故但是如果这是真的——如果事实上堕胎很广泛地被采用,在社会上和法律上都被接受,那么这将是接生婆工作中正常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她要撒谎呢?(那么为什么她的侄儿不知道她会不会打胎呢?) 她声称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堕胎,但这并不能减轻她因参与导致章杨氏之死而受的刑罚。
也许可以将相同的推理用于上述案例中的医生华群,他提供了导致朱氏死亡的栓剂,但是他也证实他并不经常处理堕胎药如果这个稳婆确实谎称她对堕胎缺乏经验,那么最可能的解释就是需要保护其他婚外怀孕的顾客这里我们只是猜测。
但是如果堕胎与社会实践和法律话语中的通奸行为紧密联系,那么在以前的情况下这个稳婆也许已经秘密地给其他处于麻烦中的妇女们开出堕胎药,在她的证词中,她也许想要使她们免于被控告和暴露丑闻的危险,因而装作缺乏这样的经验。
但是整个情况非常不同的,即并非堕胎是可以被已婚夫妇作为节育而常常实践的而且,稳婆说出真相也是完全可能的除了猜测,章宝同意付这么高的费用,没有一点不情愿,这表明他没有别的选择明显没有很多不同的堕胎服务让他选择并可以比较价钱。
第二个案例来自云南永北厅,报告于1774年,并没有报告堕胎的确切价格,但是确实表明了价格幅动的范围这个案例涉及到一名叫萧万氏的妇女,她的丈夫已经离家很长时间了她为了谋生,偶尔与比较富裕的邻居李琇(一个结婚的武生,35岁)发生性关系。
每次他付她钱100-200文,并将此关系保密七个月后,萧万氏怀孕了,她让李给了她钱4500文去买堕胎药当李不满意价格时(认为药肯定不会这么贵的),她威胁说要将孩子怀到足月,并公开孩子的父亲是李,不考虑后果。
所以他给了她1500文,答应以后会付清余额她买了一副不知名的堕胎药,虽然堕胎很成功,她也活下来,但是药物让她病倒了,并且阴道流血,在逐渐恢复之前,她有几个月没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在患病期间,她要求李给她保证的3000文余额,这样她可以支付治病的费用,但是李拒绝了,认为既然堕胎已经成功,他不再需要害怕被发现。
他的自私激怒了她,她最终从病中恢复以后,她拒绝与他再发生关系,而是与另一位答应支持她生活的邻居开始交往李开始很嫉妒,悄悄跟踪她,并最终勒死了她考虑到她与李琇的交涉,萧万氏也许花费了大约钱1500到4500文来买堕胎药 (她要求4500文,而且我们不知道是否李给她的1500文可以支付药物的全部开销)。
这一价格幅度可以与李在每次发生性关系后付的100-200文相比较:亦即她不得不跟他发生性关系8-15次来赚得这个幅度中的最低的价格考虑到价格方面证据的有限,任何结论都一定是暂时性的但是,很肯定的是我们知道价格的这8例堕胎对清朝时期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很昂贵的(毕竟,即使武生李琇也避免付 4500 钱) 。
对于穷人来说,这样的价格也许很可能是太昂贵因此难以支付这些价格也许反映了这些药物本身的昂贵,但是至少在一个案例中,关键的因素看起来绝对是堕胎服务的缺乏,这使得接生婆能勒索昂贵的服务费用事实上,费用绝不是决定易得程度方面唯一的因素。
在其它的几个案例中,人们疯狂地寻找堕胎的方式,但是不能找到,这显示出人们即使可以付得起,也未必找得到堕胎服务在一桩来自河北束鹿县的1769年的案例中,一个名叫苏氏的妇女在丈夫离家期间因为通奸而怀孕,在她的情人赵黑子无法找到堕胎药后自杀。
苏氏最初想要自杀(来避免奸情暴露的后果),但是她的情人阻止了她,要“替你去买副打胎的药来打下来吧”但是尽管他努力了,还是“寻不出打胎药来”,苏氏回到她丈夫家中服砒霜而死相似的是,在一桩1787年的来自安徽阜阳县的案例中,一个名叫贾得宝(32岁)的男人在与他的堂妹贾大姐(19岁)通奸并使之怀孕后,无法为她找到打胎药。
当大姐意识到自己怀孕后(得宝后来证实),“她叫我买打胎药”他同意了,但是发现“无处购买”在四个月后(当腹部已凸显出来),他开始疯狂避免这桩丑闻最终,他给了她掺老鼠药的酒(告诉她是打胎药),她喝下后死了既然贾得宝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有两个长工,他的妻子还有婢女),高价的打胎药也许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但是他还是无法找到。
在一桩来自广西兴安县的1773年的案例中,寡妇唐杨氏(41岁)因与临时的雇工李成忠(41岁)通奸而怀孕她雇佣他三个月,每月工资是钱400 文唐杨氏有一个干女儿赵氏,她的哥哥赵廷林是医生当她意识到自己怀孕后,唐杨氏让她的情人李成忠找到赵氏的丈夫唐明义去介绍她认识医生赵廷林,并告诉唐明义如果介绍成功的话,她答应会付银一两给唐明义,所以唐才同意帮忙。
但是当唐护送这个寡妇去赵家时,这个医生拒绝开打胎药,说“是犯法的事”唐杨氏坚持让他给出打胎药,但是他固执地拒绝了她留在他的家里,拒绝离开,他让自己的母亲过来夜里陪着她在整整两天的僵局过后,唐明义将她接回家,并告诉她的婆家人(听说了她怀孕的消息后)已经杀死了她的情人李成忠。
唐杨氏性格非常坚强,并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但是她找不到堕胎的方法这个医生的拒绝则既撩人又明显:不幸的是,他的证词并没有记录他是否知道怎样堕胎,也没有表明他认为什么是“犯法”的(例如,是所有的堕胎?还是只为通奸者提供堕胎?)但是他的拒绝是肯定的。
唐杨氏明显不知道其他方式来堕胎,因为她最终一直将胎儿怀到足月,并生下了死产的婴儿她当时被控告,然后因为通奸被杖责这三个案例中各有其特别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牵涉的全部因素但是很清楚的是,这些妇女如果有办法的话,她们是想要终止怀孕的。
而且,(更不用说的是)首先她们缺乏有效的方式避孕如果一位妇女负担不起堕胎药,或者因为别的原因不能找到堕胎药,她会做什么呢?在一桩1762年来自河北任丘县的案例中,寡妇马氏(27岁)与雇工李安(25岁)有染后怀孕,于是试图通过自我损害而堕胎。
她绝望地试图防止她丈夫的兄嫂发现她通奸的事实,因为她害怕他们会将她逐出家门,并收回她亡夫的财产和孩子李安后来证实道,“她说,‘不好了我有了胎了,你也不管我,快给我躧躧罢,’他就仰在炕上,小的上去给他躧了两三脚”。
但是当时马氏的嫂子突然撞见他们,立刻意识到马氏一定试图要堕胎马氏和李安给她的嫂子磕头,乞求她不要将秘密透露给丈夫,但是当她拒绝后,这对情人决定一起自杀李安随后谋杀了马氏、她的嫂子和她们的两个女儿,并准备自杀(但失败了)。
李被判处凌迟处死,因为犯了“杀一家三人以上”罪马氏和李安企图使用的堕胎方法的简陋,反映出这对情人的绝望与缺乏选择这让我们想起韩华的那些接受采访者,她们试图用织布机的敲击棒打击腹部来打胎这些方法几乎肯定不奏效,明显是很危险的,但是如韩华的接受采访者一样,这对情人明显无法找到其它方式来终止怀孕。
但是,有趣的是,当她的嫂子看到李踩在马氏的腹部时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对这样的行为明显再无其他解释这一例子让我对清朝司法档案中出现的许多女性“自杀”的案例感到好奇许多案例涉及年轻的农村妇女,她们吞下在农村地区容易得到的毒物后死去:例如砒霜 (用来做杀虫剂和治疗皮肤疮)、盐卤以及某些野生植物,如“断肠毒草”;在十九世纪例如鸦片。
这些死亡中的大多数无疑都是真的自杀,但是我怀疑(即使没有确切的证据)至少一些也许是因为女方试图打胎,又无法找专家,所以绝望之下求诸手边的毒药来自行打胎当然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这种行为模式(例如,1973年人工流产终于合法化之前的美国)。
在这些案例中,实际的情况也许被忽视了,或者家庭也许试图掩盖例如,在一桩1824年来自河北鹿县的案例中,一位因通奸怀孕的妇女吞下官粉而死——死因被解释成自杀,但是毒死她的成分,虽然广泛使用,却传统上被认为是有堕胎功效的。
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明确知道这位妇女的意图,但是她也许要试图打胎事实上,这种猜测可以延伸到今日的中国,农村持续保持惊人的青年妇女高自杀率,喝杀虫剂是最常见的死因之一那么,其中的一些死亡也是试图堕胎的结果吗?。
(四)因通奸而怀孕的妇女不得已而怀到足月在我见到的每一个记录实际堕胎企图的法律案例中,更多的是不便的怀孕生育的例子,这对那些通奸因而被曝光的女性有着毁灭性的结果这些案例中的妇女包括许多堕胎案例中可见的人物: 寡妇、新娘、尚未成婚的童养媳以及丈夫离家的妻子,偶尔也包括尼姑。
下面是1736年来自刑科题本的三个例子:在江苏长洲县, 寡妇邱氏的怀孕暴露了她与夫弟的奸情,这导致他们两个都因乱伦都被判处死刑;在山东临清县, 一个名叫骆氏的年轻新娘在刚刚结婚后4个月就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这激怒了她的丈夫,因此谋杀了她和婴儿;在福建南靖县,一个名叫庄氏的年轻女人在未婚夫去台湾的时候怀孕了,事件暴露后,导致她的绝望,所以她最后选择自杀,而不是面对后果。
这样的例子还有更多这些案例可以作为一种对照组(control set),与那些记录了实际的堕胎尝试的进行比较——比如唐杨氏 (医生拒绝帮助她,所以她只好怀孕到足月),如果这些妇女可以找到办法的话,她们肯定已经终止了自己的怀孕。
另外一件事也很清楚:如果她们都有有效的避孕方法的话,她们就不会让自己处在这样的窘境之中了考虑一下1845年河北宝坻县寡妇胡氏的案例胡氏在丈夫死后三年生了一个孩子,这促使她的婆家人要将她赶出家门;她反抗并否认她有通奸的行为,并声称她也困惑不解为什么会怀孕。
这种争执发展成一桩难以处理的诉讼案件无人相信这个寡妇的故事,但是她一再坚持,最后一个协调的解决方案是给了她大部分她所要求的东西(没有人可以指出她通奸的对象是谁,这也很有帮助)这个婴儿(女婴)出生后不久就死了:一开始,胡氏在公堂上承认她杀死了新生儿,她的婆家人也可以作证;后来她又改变了证词,并声称婴儿只是自己死了而已。
当事的地方官并未追究婴儿是怎样死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没有人需要它堕胎,如果可能的话,本会为胡氏省去很多麻烦事实上,如Elizabeth Johnson和韩华的接受采访者以及程茂先的妻子一样,她也许会试图
堕胎,但是没有成功在1788年发生在广西苍梧县的一桩案例中,一位妇女服下了不知名的堕胎药(她的情人付了钱4100文买来的),但没有什么效果她最后生出了孩子,然后掐死孩子后将之埋葬,徒劳地想要掩盖所发生的一切。
在涉及不需要的怀孕的法律案例中,牵涉溺婴处要比牵涉堕胎处普遍得多这表明在可能的时候,溺婴也许是处理这类问题首选的解决方式我们从一桩1737年的湖北巴东县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计算中得到启示,一名名叫谭氏的妇女在娘家长时间停留照顾生病的母亲时,因为通奸而导致怀孕。
她的情人付给她父亲钱让他容忍他们之间的关系她的情人心里想她也许可以诉诸于堕胎或溺婴的方式于是他警告她的父亲,并表明他要孩子,若是怕(她的丈夫)李文明知觉,或将身孕用药打下,或是产后淹死,(我)就要向李文明实说“卖奸怀孕,大家弄得不好开交”。
这件事得到官方的注意的原因是,谭氏的情人杀死了她的丈夫,希望将她据为己有,那时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谭氏的情人的陈述表明,堕胎和溺婴是两种处理不便的怀孕的可能方式事实上,谭氏确实要回到丈夫身边(对她来说,这桩奸情只是一时的风流韵事,并不是长期的关系),所以她并非她的情人的同谋。
当在公堂上被审问时,她解释说她已经计划将回到丈夫家的时间推迟到下个春天,因为“产后不难灭跡”,她的丈夫将不会发现这个陈述暗示了她在排除了堕胎的可能后打算溺婴但是溺婴要求一位妇人先生下孩子分娩本身有着风险(考虑到产妇高死亡率),不过,更危险的是,分娩很难隐瞒——对于一位想要保守秘密的妇人来说,这可能是主要的问题。
例如,在一桩1736年来自安徽寡妇秦氏的案例中,秦氏与她的雇工发生性关系后怀孕了,产下婴儿后立即将其掐死但是她警觉的邻居听到了新生儿的哭声,所以她的通奸行为暴露了她选择自杀而不是面对被控告和被婆家驱逐的境况。
在另外一桩1736年来自河南滑县的案例中也有相似的情形,寡妇刘氏(她与两个邻居男人有染)在孩子一生下来就处理掉,但是她的偷窥的公婆发现了尸体——当这个寡妇试图逃走时,他们将其抓住并杀死了她考虑到她们所冒的风险,为什么秦氏和刘氏将婴儿怀到足月呢?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她们只是别无选择。
三、近代中国不安全的堕胎(一)传统的堕胎方式在河北,1928年不安全的堕胎并没有随着清朝的覆灭而消失反之,一直持续到整个20世纪,甚至在改革开放时期一位英国的医学传教士J. Preston Maxwell对华北的传统堕胎技术颇富洞见。
他当时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产科学和妇科学教授1928年,在《关于中国的犯罪式堕胎》一文中, Maxwell以骇人的细节描述了他治疗这些堕胎行为带来的有害后果的门诊经验Maxwell 描述了四种基本堕胎方式第一种是“从外部剧烈按摩子宫”,他认为这种并不是很常见或有效的,“这个过程几乎成功率很低”,“这个方法的成功率很低,主要的效果只是让腹下部很敏感而已”。
在世界上的一些禁止堕胎的地方,按摩堕胎还在实践之中,但成功率很低,患上并发症的几率很高我没有见到有关按摩堕胎在中国很普及的证据Maxwell引用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是“以外物插入子宫颈”以及“催生针灸”,穿过皮肤和腹壁将针插入子宫。
Maxwell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是偶尔使用但是,如众所周知的衣架堕胎一样,它们有着威胁生命的严重危险,在杀菌和抗生素缺乏的情况下,这样的进入体内的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是“正确无误”地做Maxwell报告了另一例成功堕胎的妇女将筷子插入自己的子宫颈中,这之后她差点死于败血病;第二位妇女尝试这种堕胎方式失败了,但是她确实死于破伤风。
他也讲述了三个针出现问题的病例其中的两例中,针断了或者留在腹中,需要实施紧急的外科手术拔出来这两个女人都没有成功打胎另一名妇女 (38岁的农民,因为在丈夫离家时通奸而怀孕)在雇佣一名“中国传统医生”使用针灸之前,最初尝试过草药堕胎而无效。
(在较不危险的方法失败后,她采用更加切入也更加冒险的方法,这是世界上普遍记录的不安全的堕胎模式) 在第三个病例中,一名43岁的寡妇(她已经怀孕8次了,这一次是因为通奸而再次怀孕)在被针刺了总共四次之后成功堕胎;但是后来她死于腹膜炎。
Maxwell引用的第四种方法是堕胎药,所有证据显示这是主要使用的手段Maxwell的一个接受采访者是一位中医,此人提供给他堕胎药的三个处方,并肯定它们在怀孕的前三个月都很有效第一个处方主要包括毒虫:斑蝥14只、红娘虫两只、水蛭5.6克、虻虫1.9克等成分,研磨成粉,与酒混合后口服。
这个处方应该是危险的,因为中国的药物杂志报道了仅服用三只斑蝥后妇女即死亡的案例第二个处方将麝香与几种煎煮过的草药混合,随酒口服第三个处方是阴道栓剂,由麝香和其它药材研磨成膏状,并将之放入绸袋中Maxwell 注意到“我们接手的相当多病例是受害于这些药物的后遗症,这些药物的使用范围在全华北地区。
”他详细地描述了两个栓剂带来副作用的病例在第一例中堕胎成功了,但是导致这个妇女生殖器官的永久性损伤:“从那以后,每次都会有严重的月经困难,随着黄色排出物和血液排出,疼痛也停止了阴道被强烈的纤维组织阻塞……子宫被覆盖在粘着物中,阴道变得非常窄。
”在第二个病例中,堕胎失败了——Maxwell相信这个女人几近死亡,虽然他不知道她最终死了没有他也引用了其它两个病例,其中妇女死于肾衰竭,虽然他没有指明具体使用的是哪种堕胎药在这些妇女中,Maxwell所报道的具体情况都是因为
通奸而怀孕在这方面,他的证据与清朝记录堕胎企图的法律案件有着令人生畏的相似性:共同的主题是这些妇女之所以拿生命去冒险,是因为她们害怕婚外怀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应该注意的是Maxwell所使用的术语——“犯罪式堕胎”(criminal abortion)反映的事实是,在他写作的民国时期中国法律是禁止人工流产的。
Maxwell的主要考虑是这些简陋的堕胎方法“对病人带来的极大风险”,他将之称为“一个严重的威胁”当然,像法律案件一样,Maxwell的证据是轶事型的;如知县一样,一个医师可能只会接触到危险的堕胎事件尽管如此,如法律案件一样,他的证据反驳了对传统堕胎技术所有的过分的信心;至少,这向我们表明,任何人都要承担证据方面的压力,如果他们要承认这样的技术安全或可靠因而可以经常使用的。
(二)1949年以来的传统堕胎技术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为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原因不遗余力地促进中医发展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强制型生育控制来限制人口增长因此,如果1949年以前安全可靠的堕胎技术得以普遍使用,我们将期待这些技术继续在今天被广泛使用。
那么,传统技术的现代命运如何呢?近些年来,许多草本堕胎药已经在精心安排的临床或实验室条件下进行检测,有时候使用未加工形式,但常常是使用可以注射的化学提取物看起来最大的成功来自于这些传统药剂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例如,20世纪70年代天花粉中的提取物(叫做天花粉蛋白),与前列腺素一起使用,(通过注射)在怀孕早期进行堕胎,报告成功率是81%但是后来,天花粉蛋白大体上被米非司酮取代,效果更加令人满意米非司酮是今天中国首选堕胎药,虽然只是偶尔以传统疗法辅助治疗。
例如一些医师报告了成功使用牛膝根来膨胀子宫颈,与米非司酮或者外科堕胎一起使用;另外一些声称成功使用含有麝香的腹部膏药来提高有效性并减轻米非司酮的副作用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记述,是关于成功使用现代中医门诊开出的传统药方来堕胎。
但是医学杂志也包含许多不满意或者有害结果的记录例如,一位医生报告了他使用两种不同的用麝香、牛膝和其它成分煎煮的草药来尝试堕胎:这些药物没有什么效果,病人最后需要外科手术堕胎另一位医生在41 个不同的病例中使用三种有名的传统制剂来堕胎,失败率是百分之百。
但是,在一个很说明问题的评论中,他提示说“在实验中使用的制剂是因为安全起见被筛查,但是危险成分如水银和斑蝥被除去了”似乎通过除掉明显的有毒成分,这位医生降低了这些制剂中可能有的任何堕胎功效相似的是,其他的两名医生报告了打胎失败的例子,即用一只斑蝥,用温水口服,这是《本草纲目》开出的“下死胎”的药方。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安全剂量的斑蝥作为堕胎药是完全无效的,高剂量的就只会太危险以至于不能尝试这些证据是轶事型的,但是它们表明谨慎注意安全方面的医生已经发现传统的未加工药物以作堕胎药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对比而言,1986年报告的一桩病例涉及一个怀孕5个月的18岁高中学生,乞求校医帮助她堕胎。
这个医生使用含有一只斑蝥、水蛭、虻虫以及瞿麦的药方,煎煮后口服当这个药方打胎不成功时,这个医生让学生又服用了三次,每次少量增加了斑蝥的剂量,但仍然没有效果最后,在沮丧中,这名医生让她服用第五次,这次他用了。
30个整只斑蝥—— 这个剂量毒死了她验尸的法医估计被摄入的斑蝥总量已经超过了致命剂量的五倍(三)不安全的传统堕胎药的持续存在上面三个涉及斑蝥的例子让我们注意的是安全的问题斑蝥是传统上用来堕胎的最危险成分之一。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见,许多传统的堕胎制剂中包含斑蝥、芫青以及虹娘虫, 有时也一起使用我们发现《金瓶梅》中潘金莲使用的堕胎药中含有的斑蝥,同时也出现在Maxwell中报告的堕胎药方中的一个 (与红娘虫调在一起)。
即使今天,斑蝥被普遍认为可以堕胎,同样可以治疗狂犬病与癌症结果,因为摄入斑蝥而中毒或导致死亡始终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依据广东中医大学的两名教职人员的说法,斑蝥中毒通常起因于“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所使用的“民间偏方”。
但是这样的迷信并不限于农村的穷苦人民,可见下面的由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史学家发表于2004年的声明:我曾听一位当事人讲,她一次因偶然带了一块麝香,从此就不能怀孕(她因为已有四、五个小孩,也就“歪打正着”,
乐得如此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将一种药物“斑蝥”置于子宫颈口(似用一纸捻送入) ,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一方法, “从良”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如果一位在重点大学执教的教授尚且认为这种危险的无稽之谈有几分道理,我们不应该惊讶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也会这样相信。
斑蝥素(斑蝥、芫青中的活性剂)是有强烈腐蚀性的,可以被外用作发泡剂;在中医中,斑蝥可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粉状的昆虫可以涂在皮肤上(例如除去瘊子)但是不小心使用或者吸入粉末,可以引起严重的化学性灼伤——对于一位将斑蝥塞入子宫颈中的妇人这将是一场灾难。
当然,绝望的妇女想要防止怀孕或者终止怀孕而这样使用它是可能的——毕竟,在美国人工流产合法化之前,妇女将漂白剂或碱液灌入阴道来试图堕胎是很普遍的事情,即使这常常是致命的我还没有找到目前用斑蝥试图堕胎而中毒的发生频率的统计数字,所以我的证据也是轶事型的。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并不缺乏关于这样事故的报道,包括很多致命性的例如,山东单独一家医院在1989到1996年间就为86个这样的独立病例提供急诊护理山东的另一家医院在1997到2001年间处理了42起这样的事件。
一些中毒起因于试图治疗犬咬伤或者癌症,但是很多受害者是希望中止怀孕的女性:一篇2004年来自河北张家口的报道这样说,“斑蝥中毒可见于多种原因,但以未婚年轻女性怀孕误用其堕胎最常见”在我对在线医学刊物的粗略调查中,我发现关于这样的报道来自北京、甘肃、广东、贵州、河北、香港、湖北、江西、青海、陕西、山东、四川、天津和云南。
在我已经见到的报道中,每个成功堕胎的女人后来都死掉了,而那些活下来的则堕胎失败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一篇发表于1990年的文章中,文中报道了两个湖北农村妇女的病例,两人均未婚,都因试图打胎导致斑蝥中毒而死。
第一个女人21岁,怀孕7个月后,她深夜一人喝下掺有斑蝥粉的酒,天明就死了另一个女人,22岁,怀孕四个月,她口服了六个粉状的斑蝥,也将含有另外四只斑蝥的粉末的膏药贴在太阳穴和小腹上24小时内她就死了一篇1999年的来自广东的报道描述了一个未婚的21岁女人,怀孕三个月,喝下大约半两斑蝥煎制成的药汤。
虽然她得到急救治疗,但是在24小时内也死了斑蝥在这种病例中绝不是唯一的肇事原因,我们也可以找到麝香和各种各样的草药堕胎药引发的中毒报道例如,一篇1986年的文章报道了来自桂林的一桩病例,一位24岁的未婚女人,怀孕2个月了,使用了一扎白花丹记在红线上作为阴道栓剂。
她从一位没有执照的中医从业者处得到了这个草药,俗称“土牛膝”在插入栓剂两天后,她堕胎成功了(在一间公共卫生间),然后就晕倒了,被送进医院治疗失败了,几天后她死于肾衰竭这样的描述,都与清代法律案例和Maxwell的1928年报告的情节惊人的相似。
大多数都描述了因为害怕将婚外性关系暴露于世,因而求助于绝望的手段西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网页包含下述声明,题目是“切忌自服打胎药”:妇女怀了孕,因为某种原因想把胎儿打下来,又不好意思去医院做人工流产,所以想自己吃药打胎,这是非常危险的。
容易造成大流血、不全流产或遗留妇科疾病,这是常见的因为打胎药毒性大、用量大,更容易引起中毒农村用中药斑蝥打胎一般成人口服斑蝥粉0.6克即可产生严重的毒性反应,口服1.3-3.0克即时可致死主要毒性物质为斑蝥素,内服可引起胃肠炎症,粘膜坏死;吸收后可引起肾小球变性、肾小管出血;心肌也出血;可引起神经系统损害。
有的用牛膝、附子、麝香、夹竹桃叶等纳入阴道,企图造成流产,常常导致阴道大出血而危及生命还有些中药:如马钱子、生南星、生川乌、生草乌、水银、巴豆、蜈蚣、水蛭、三棱、茂术、益母草等药用来打胎对孕妇带来不良后果。
这里我们有了关于今日中国不安全的传统堕胎方式的简单陈述,包括长期使用的许多最危险的成分的清单认为中国没有任何变化的观点肯定是错的,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在产妇保健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根据政府统计,中国的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每100,000例活产中94.7例产妇死亡到2004年降到48.3例。
今天,安全避孕和堕胎在中国非常普及——因此不安全堕胎的几率被视为微不足道的,尤其是与禁止堕胎或者不提供堕胎的国家相比尽管如此,非安全堕胎导致的死亡明显没有被充分报道,事故很难被估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且,考虑到今日中国农村年轻妇女相当高的自杀率,也许这些“自杀”中至少包括一些不安全堕胎导致的死亡,这并未被承认或故意谎报。
正如西安政府网页指出的,大多数斑蝥堕胎中毒看起来涉及的是那些“不好意思”去门诊堕胎的年轻农村妇女民意调查显示,迁往城市的农村移民越来越对婚前性行为无所顾忌,并愿意得到安全避孕和堕胎的措施,但是在他们的家乡,对这方面的态度却可能很严厉。
一群于2001年在贵阳接受采访的农村妇女解释说,婚前怀孕是禁忌,“没有人敢在婚前怀孕!老人如果发现会将你踢出家门!在城市不是个问题,但是在乡村却很重要整个家人都会丢脸!”明显还没有变的是:至少一些妇女仍然害怕暴露婚外性行为,并到了这样的程度——她们不敢冒被发现的危险去安全的诊所堕胎。
相反,她们诉诸于不安全的传统堕胎方式,后果我们已经见到了偶尔可以在今天的媒体报道中看到使用传统打胎药而中毒的病例,这对我们的调查有意义,主要的是因为这使我们容易理解过去堕胎是怎样被尝试的这些报道使我们得以一瞥旧的材料记载的行为在今天的状况。
如果因为传统方式导致的不安全堕胎在今日中国并不常见,那么这是幸运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到最近为止,这些传统方式是唯一可得的方式。
结论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范围内大约每年500,000 妇女死于与怀孕有关的病症,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是由不安全堕胎引起的在与堕胎有关的死亡中,98%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成千上万的其他的妇女受害于不安全堕胎引起的并发症所导致的身体健康受损……因此,不应该对民间传统堕胎方法的安全与可靠性有乐观情绪。
田野调查的报告使这些数字变得形象起来例如,在乌拉圭(堕胎是违法的),1986到1999年之间,一家毒药防治中心为86名由于服用草药堕胎药而患重病的妇女提供了急救护理这些打胎药中可以指明的有30种不同的植物成分;11名妇女除了吃草药外也尝试了自我伤害。
这些妇女中仅有23人成功地打胎,但是14人遭受了多种器官衰竭,9人需要进行子宫切除术,还有5人死亡许多其他妇女健康方面遭受了严重而持续的损害“大多数(确实成功的)堕胎行为发生在已经有多种器官衰竭和患有肝脏或血液疾病的病人身上。
这些结果强烈表明大多数堕胎发生在草药中毒的情况下”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之下,堕胎“成功”就是中毒的副作用而已这个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摄入植物来打胎包含了严重中毒的风险,这很可能将导致死亡或未来的生育并发症”。
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声明堕胎在明清的中国被用来进行常规性节育;这些学者之间尽管有不同之处,但是都似乎以为传统的堕胎方式安全、有效,对希望堕胎的妇女来说是容易得到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说法将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产生深刻的意义。
中国人也许是在现代医学来临之前,世界上唯一享有这样有效的生育控制的人民事实上,我相信中国并非例外1949年以前堕胎在中国的实践实际上看起来相当熟悉:看起来很像人工流产合法化之前的美国;看起来也很像乌拉圭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仍旧广泛存在不安全的堕胎行为,经常依靠草本混合物与切入或自我损伤的方式。
中国现在留存的民间方法是符合以上论述的,亦即这些方法都很危险且不可靠 安全可靠的避孕与堕胎是现代化所提供的最大益处之一,但是如其他益处一样,这并非可被全世界普遍享有因为禁制、耻辱、贫穷或其他因素,还有一些地方无法得到,绝望的妇女继续诉诸于不安全的传统方式——连中国好像也包括在内,虽然中国已经在保护产妇安全方面取得了全面的进步。
全文完~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欢迎长按二维码关注“女史”公众号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