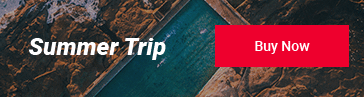没想到红花子(红花子图片)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3-08-16
近日偶回乡下,江南的冬日虽依旧是山明水秀,但朔风扑面,仍是能感觉出一些冬的萧索味儿。尤其是收割之后的稻田里,满目都是齐膝的稻茬,以及收割机直直的
.jpg)
近日偶回乡下,江南的冬日虽依旧是山明水秀,但朔风扑面,仍是能感觉出一些冬的萧索味儿尤其是收割之后的稻田里,满目都是齐膝的稻茬,以及收割机直直的驶过或者是转弯时留下的深深浅浅的痕迹就像是刻意在画板上涂上的工艺性的线条,了无生趣。
而或挺立或偃伏的稻茬由起初的饱满的金黄逐渐变得浅黄进而变成干瘪的灰白我明知道生命极致的高潮过后结局大抵如此,也难免一丝若有若无的失落萦怀面对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的故土,脑海中少年时期的田野景象便逐渐灵动鲜活起来。
彼时的山丘基本都是光秃秃的,冬日的田野也要显得干净许多寂寞的北风仿佛因为缺少繁茂的枝叶应和而显得无精打采,甚至都压不住调皮的孩童们头顶升腾起来的热气,也钻不进他们沿袭自兄姐的宽大的衣袖与趿拉的鞋跟他们是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为数不多的活跃者,当然还有四处觅食的麻雀,喜鹊以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儿。
空旷的稻田里,稻茬在泥地上几乎没有剩余,只留下一个个镰刀收割过后细小的孔洞因为稻草也是那个年代里农村颇为珍贵的资源之一喂牛,垫床,垫猪栏牛栏,引火,编草鞋草绳,还要预留整齐而品相好的作为来年插秧之前的捆秧草。
如果办什么大事家里来了较多的客人,铺开几捆稻草,几乎就可以完美解决小伙伴们的留宿问题了因为稻草而流过的汗水以及经受的煎熬,相信所有从农村走过的70后以及之前的人们都深有体会,这里不做赘述但是,也许土地天生的会不甘寂寞,也绝不会长时间容忍空空荡荡。
总有一些生命会在不经意间潜滋暗长,时间一长,便逐渐形成另一番独特的风景笔杆草,油毛毡,鸭舌草,烂絮草,马绊筋,黄花子草,蒲公英,车前草,丝茅草,还有些不知名的小草总是会争先恐后的冒出来,密密麻麻的挤占这片土地,填补秋收过后田野的空白。
它们生命力极顽强,几乎可以说是百折不挠地吸取着土壤的肥力,坚韧不拔地为大地披上一件百孔千疮的并不华丽的冬装而那些一贯勤劳朴实的农家汉子却做不到对它们的恣肆坐视不管由于当时肥料有限的制约,他们开始发挥他们的智慧,播撒一种我们叫做“红花子草”的种子。
这种种子实际上大概应该叫紫云英吧,从里到外都呈油亮的黑色,有弯月形的荚壳包裹这些种子附着到土壤表层,就逐渐发芽生根,然后就声势浩大的蓬勃起来尤其是那些在收割之后不久就被播撒的田地里的红花子草,长势凶猛,那些杂草几乎是无立足之地的。
只有被粗心的农人忽略的地角或者是草籽播撒不均的地方才是它们放飞自我的乐土每年正二月春耕时节,田野里几乎满是红花子草的身姿:茎杆不过半尺许,略带绛紫,油润而匍匐,叶片密密丛丛,花朵小小的,花冠上部呈紫色,靠近花萼部分却是白色,六到八个花瓣略向四周伸展,有着淡淡的香气,混合在开始翻耕的泥土以及春日阳光的气息里,似乎周围的一切都氤氲在慵懒得让人昏昏欲睡的味道里。
要不是春水淙淙鸟雀欢跃,泥地上太过湿润,我感觉随地都可以让我打盹红花子草本来就是充当生态肥料的,锃亮的犁铧插入泥土,沉默的老牛奋力前行,赤脚的老农头戴光油斗笠,嘴含“喇叭筒”,右手扶犁左手牵牛绳,再挥舞竹枝牛鞭,时不时再呵叱几声,咒骂几句,泥土便翻转着油亮的肚皮整齐的一道道的排列在阳光与泥水中了。
红花子草便随着泥土的翻转深埋起来,腐烂,而后就为水稻的生长提供肥力至此,它美丽的身影就此湮没,只待来年再次妖娆了之所以清晰地记得这些,其实还有另外的原因其时,农家每户基本都要养上一头两头猪的一则可算是一种颇为原始的积蓄,孩子读书或者红白喜事,有头猪基本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了。
二则寄托了农人对丰年的一种希望过年时节,宰上一头肥猪,卖掉一大部分填补生活的窟窿,留下小部分做点腊肉,或者提上一块两块走亲访友剩下一些猪头猪脚猪下水,则在宰杀“年猪”之时,遍邀亲友“喝血酒”,就着烧旺的炉火和烫温的米酒,燃几支香烛,点一挂鞭炮,既感恩天地祖宗的庇佑,又犒赏自己一年的辛劳,同时也感谢亲友的帮衬,在当年的乡村里也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
如果哪家哪年没有“年猪”可杀,他家的人过年时的声气都没有那么响亮的由于我家喂养的猪每年基本都填了“书袋子”,这种不快是体验了太多的那时养猪周期一般需要半年左右没有饲料(即使有也买不起),粮食用于糊口尚显不足,显然是不可能拿来喂猪的。
喂猪的主食基本就是红薯藤,烂白菜叶,萝卜叶等等,偶尔拌点潲水谷糠但这些蔬菜都有它的季节性和生长周期,所以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上学之余都有一个重任:打猪草放学归来,书包一扔,就背上草篓,带上一把镰刀向田野四散飞奔。
除了传说中的水母藤有毒,丝茅草太硬,油毛毡扯不起,车前草太苦之外,其余的野草差不多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草篓其中的黄花子草尤其是最佳选择在油油的泥地上,两三寸高的茎杆顶端开出一朵明亮的不到小指头大的黄花,花蕊攒聚,毫不起眼。
茎叶通体绿色,最低的一层叶子紧贴地面,大概能有鸡蛋大小看到它的踪迹,我们都会两眼放光,小心翼翼地伸手归拢叶片,然后连根拔出这种草通常都有肥大的根系,当然也可能是因此而成为了猪的美食当然,红花子草虽然茂盛,茎杆汁液足,味略甘(曾经偷尝过),但绝不可以放入草篓的。
可能是农人把它当成了一种经济作物,是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采红花子草喂猪是损公肥私,是被严厉禁止的于是,在繁茂的红花子草中间,我们都自觉地睁大眼睛辛勤寻觅黄花子草等杂草的踪影待到野草堪堪填满或大或小的草篓,小伙伴们就逐渐聚到一起来了。
嬉笑打闹,追逐玩乐很多时候都会玩一种“打杈”的游戏找三根尺许长顶端带杈的小木棍搭在一起,隔三米左右的距离画一根线,就可以开始游戏了小伙伴们先通过“铜锤剪刀布”的方式决定参与的顺序,一切就绪后,参与者站在线后方拿镰刀掷向搭好的木棍,然后根据木棍散开的形状判定胜负。
小木棍依次散开并排为最佳,排列不整齐者次之,互相有牵连或者干脆没有掷中者为输家一轮下来,一般输家都要向赢家“进贡”一把猪草的简单而并不严密的游戏让那时的我们乐此不疲虽然偶有争执,但很少有人耍赖,因为谁都明白一个道理:与被孤立和失去玩伴相比,一把猪草的价值简直不值一提。
当然也有时有的小伙伴“进贡”得太多,回家前就只能再胡乱扯上几把杂草,或者就干脆弄点树枝塞进篓底充数这一招自然是无法糊弄父母的,于是,在暮色四合的小山村里偶尔就会从哪家昏暗的油灯下传来大人的怒吼和小孩尖细的惨叫声。
但是好像却从来没有影响过第二天同样的剧情的上演在同样的一片田野上,红花子是正统,是嫡系,是需要呵护与尊重的,而黄花子等则是旁支,是杂牌军,是可以随意采摘践踏的少年时这种朴素的认知深入骨髓,至如今我也说不清楚它对我们这一代或者几代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常听乡间的老人们说起“草籽命”,意即绝大多数的人不过就像是草耔,老天把它撒在哪个角落,它就在哪个角落落脚,生根,发芽,长成,开花,结果,待秋风起时,便寂然枯萎,飘零,归于尘土而今细细想来,这种说法还是有很多漏洞的。
首先,草籽与草籽是不同的,比如红花子与黄花子其次,当代社会里人员的流动性远非昔日可比,人们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也增加了不知多少倍但是,有一点却让我高度认同: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在有限的生命长度里,尽可能的展示生命的艳丽,活出生命的精彩。
那么,不管是红花子还是黄花子,都已经心无所愧,得其所矣是夜,听着从老房子旁边大樟树枝头呼啸而过的朔风,我安然入梦。梦里我重新背上草篓,走向了遍野的红花子和黄花子……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